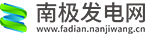
传播中的误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权”话题在时尚中的风行,近年来关于法国导演阿格尼斯·瓦尔达电影作品的谈论,明显地多了起来。
关于阿格尼斯·瓦尔达,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一直有两个误读:
 【资料图】
【资料图】
第一个误读,是称瓦尔达为“新浪潮老祖母”。这一下子辈分就上去了,而且有些文字进而以讹传讹,直接给传成了法国新浪潮电影之母。阿格尼斯生于1928年,比出生于1930年的戈达尔大两岁,比生于1932年的特吕弗大4岁,4岁的年龄差,不至于当同辈人的“母”或“祖母”,挨边儿一点的宣传语,恐怕应该是——“来自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老祖母”。
第二个误读,是阿格尼斯·瓦尔达与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关系。关于“新浪潮电影”,世人历来都是广义内涵和狭义内涵混用。广义内涵是指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法国非商业电影,这里面包括了在世界影坛大放光彩的新浪潮电影、审美更加私人化和实验性的左岸派电影(代表人物有阿仑·雷乃、阿兰·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及瓦尔达的丈夫雅克·德米),以及与这些流派同时期争辉的一些杰出导演(如让·克劳德·勒鲁什、贝特杭·布里叶等人)。狭义内涵当然是指作为流派的新浪潮电影(电影手册派),代表人物是戈达尔、特吕弗、侯麦、夏布洛尔等人。
一般来讲,阿格尼斯·瓦尔达,因其老公雅克·德米,以及本人作品强烈的人文气质与实验性,往往被影史归入到更具实验风格的左岸派影人行列。不过左岸派的多数电影,不是作家出任导演,就是作家担纲编剧,文人气质过于明显。瓦尔达自己的影片,与其说文人气质强烈,倒不如说它们更强调作者视野。这样一来,倒更靠近戈达尔和早期特吕弗的风格,这也构成了阿格尼斯·瓦尔达作为导演的流派身份模糊感。许多误解由此而来。
辐射面广阔的代表作
与流派身份模糊形成对比的,是瓦尔达的一生荣誉辐射面之宽。她拿过金狮奖(《流浪女》),晚年又先后拿了戛纳和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还拿过欧洲电影奖与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荣誉与其夫雅克·德米(以《瑟堡的雨伞》获金棕榈奖)以及戈达尔、特吕弗这三位影坛宗师不相上下。同时代影人中,所获重量级奖项仅稍逊色于左岸派首领阿仑·雷乃。但她的作品量可比阿仑·雷乃少多了,所以,若单以获奖级别和次数作为衡量一生成就的尺子,阿格尼斯所达到的高度,是会把个别人气死的。而且她的成功,还属于无规律可循、不可复制的那种。
阿格尼斯·瓦尔达的影片,题材跨度不小。成名作《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风格介于剧情片和精致的纪录片之间。它讲的是年轻女歌星突然被告知可能得了重症,在焦急等候确诊结果的两个小时间的行为。该片入围了金棕榈奖,虽未获奖,但它细腻、缜密、冷静的叙事,对于女性角色在呈现时不动声色的体贴,都带有比较鲜明的人文属性。它也更靠近电影手册派导演们的作者气质,而不像左岸派“作家电影”那样更偏于极端和审美的私人化。
摄于1977年的《一个唱,一个不唱》,是被评论家较多解读的一部电影。该片围绕堕胎、生育、婚姻这些日常话题,讲述了两位女性近二十年的命运。喜欢演唱民谣的十几岁少女宝琳娜和刚二十出头已经做了两个孩子母亲的苏珊娜,她们同样向往独立,又各有着对艺术和家庭的不同愿景。她们因苏珊娜摄影师男友拍的照片产生交集,而后又因为各自的生活轨迹分开、再重逢,各自体验并分享着情感、抚育孩子、自立生活的甘苦。全片采用双线并行叙事,宛如一首对现代生活中女性坚强的赞美诗。
1985年获得威尼斯金狮奖的《流浪女》,影像风格更趋于纪录片化,剧情采用倒叙式展开,越看到后面,越能体现出导演的匠心所在。全片以多个目击者的口吻,拼贴式重现了一位名叫莫娜的年轻女流浪者桀骜不驯的人生状态。电影一开头,主人公莫娜已经曝尸荒野了。莫娜是怎么死的?这一点既可以说是观众所抱的好奇,也可以说是瓦尔达提前翻出的底牌。不管遇到怎样具体的情况,只要是桀骜不驯的生活,必然会遭遇到多种危险和挑战,人们怎么看莫娜对这种生活的选择?这才是瓦尔达所要呈现的。这种近似于社会学家的冷静(甚至有一点冷酷),倒是又体现出了“作者电影”美学的某种特点。
1988年的《功夫大师》,也许是当代电影里较早表现那种“女大男小”式禁忌恋情的一部。但本片的重点似乎并不在于表现那种恋情与外部习俗压力之间的冲突,而在于呈现恋情中人的微妙情绪,尤其是作为年长者的女主人公的情绪,用作片名的“功夫大师”,只不过是少年迷恋的一款电子游戏,并无太特别的寓意,这种随机式的片名命名,又让电影在剧情以外自带出某种后现代式的率性。片尾处,少年已经长大,开始用一种淡然的口气,谈论终止的恋情,这依然让影片呈现出轻微的“作者电影”的残酷感。
上映于1995年的《101夜》,则一反阿格尼斯·瓦尔达上面几部的写实与“残酷”,开始讲述起一个辗转于病榻的百岁影人,幻想与现实在神智中开始不清,但他仍在挣扎着梳理记忆里与电影有关的过往,并雇了一位女学生作为助手,女孩也因此得以见到了那些老的电影文物,以及现实中的马斯特洛亚尼、德尼罗、德帕迪约、凯瑟琳·德诺芙、阿兰·德龙等著名演员……该片是为了纪念电影百年诞辰的订制作品,带着瓦尔达影片中少有的显性的温情。
在瓦尔达出色的纪录片中,《我和拾穗者》尤为值得一看,该片也是自伊文思的作品之后,纪录片领域少有的“带有现代性诗意”的作品之一。影片呈现了名画中的拾穗者,生活中捡拾食物的人,从垃圾中搜集创作素材的艺术家,出于环保或节俭或其他目的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人们……天下之大,人们的爱好及生存方式无奇不有,他们都因为一个普通的“捡拾”动作,被影像串联到了一起,构成了一部“捡拾交响曲”。
立场或误解
阿格尼斯·瓦尔达的影片,尤其是剧情片,绝大多数以女性为主人公。不少男性角色都是被置于次要位置,有的甚至可以说直接被当成了背景板,他们更多是被用作映衬和演绎女性心灵。所以不少研究者愿意将瓦尔达的电影冠以“女权”的标签。但仅仅从“女权”的角度去关注瓦尔达电影,显然会将观看的视野变窄,进而落入概念化的陷阱。
一位艺术家,她(或他)是应该着力去表现自己熟悉的人性与世界,还是努力地进行虚构和对世界的重组?对于不同的创作者,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如果对于更青睐于写实创作的影人,表现自己熟悉的人性和生活,当然是第一选择。瓦尔达电影对女性的关切,无疑是属于这种情况。
一位女导演,钟情于拍她熟悉和更感兴趣的女性题材,这难道还需要强调或硬性赋予她一个什么立场吗?打个比方:中文电影里,已故的张暖忻,健在的许鞍华,都非常青睐于拍女性题材,难道人们就非要把她们的作品放到“女权”的框子里,才能显示出其作品的价值吗?瓦尔达的电影,自然也是这种情形。不能因为她的影片直视了生活中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就硬性去作僵化的读解。艺术关注的是生活,反映的是艺术家对于生活的思考,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去进入社会学范畴的标签。过于武断地归类,实在是对创作者智慧的矮化。当然,也是对自己理解事物能力的不自信。这样的亏,人们过去吃的并不少。
关键词: